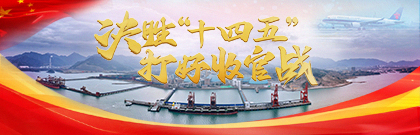喜見“大觀”重刊布 牽絲映帶落紙端
——評新版《宋拓大觀帖第六卷榷場本》
■高巖
手捧新版南京大學博物館藏《宋拓大觀帖第六卷榷場本》(文物出版社出版),摩挲展玩,興致之余,不禁憶起兒時的舊事。
1992年壬申歲初,我念初三,學習之余,常去琉璃廠文化街古籍書店看書。那時北京的書店,已經可以開架閱讀,新書都會放在較為明顯的位置,只是品種與之當下相比,遜色很多。我少年時對法書字帖的強烈熱愛,有似追星。上海書畫出版社印刷的《大觀帖》卷六,一下映入我的眼簾,王右軍流動飄逸的書寫,讓我興奮不已。然而那時的我,只有兩三元的零用錢,每次去廠肆,萬不敢任意消費,多是“過眼癮”之意。因此,四塊二角的定價足以令我望而卻步。駐足許久,也只能歸家。攢了半月積蓄,再去廠肆,除了卷六,還得了卷七。當日的興奮、不舍與滿足,今日想起,還在眼前。三十年前再精美的出版,也只不過是黑白原大印刷,由于版次之別,我當時買的那一版,已經不是初印,略有模糊,“大觀”的真面打了很大的折扣。
讀到此處,讀者會有疑惑,講述這段故事目的何在?那就用啟功先生的話來詮釋吧!先生對《大觀帖》素有?青睞,云:“編摹底本自升元,王著徒蒙不白冤。淳化工粗大觀細,宋鐫先后本同源。”按照啟功先生的話說:“《淳化閣帖》本身的底子也并不是憑空捏造的,它也有勾摹的底本。《淳化閣帖》刻完了不滿意,到了宋徽宗的時候,他就把那個底子拿來重新刻一回,就是《大觀帖》。我們試想《淳化閣帖》底子要是胡亂的底子,那大觀重刻怎么能反倒精彩多了呢?可見勾摹的底子并不那么壞,《淳化閣帖》刻的時候潦草,而《大觀帖》刻得精細,底子還是那個底子……可見《淳化閣帖》那個底子有重刻的價值,所以宋徽宗大觀時候摹刻的,只是用精致的方法再刻一回,好比我們現在有影印本,有的影印本很模糊、很不好,我們用精致的印刷的方法,再印一回,底子還是那個底子,可是效果就不一樣了。”
這里說的《淳化閣帖》和《大觀帖》,就好比故事中黑白影印本和這次文物出版社彩色精印本的區別吧。《大觀帖》自1942年4月起,至2001年啟功先生主編《大觀太清樓帖宋拓真本》九冊黑白影印,再到2002年3月,啟功先生主編《中國法帖全集》彩色縮小影印,這些影印本,皆由于當時印刷技術、出版體例的原因,是有所缺陷的。可以說從初印到本次印刷之前,已有八十余年,這冊精印,意義深遠。
高線掃描,數次校樣。本次出版,采用六百線數掃描設置,印刷再降至三百線數。讀者翻閱拓本,可以感受逸少書寫牽絲映帶的細微之處,這除了“大觀”刻工優于“淳化”之外,更有賴于出版社對印刷把控到位。
正反施色,配之插函。精準校色之后,印刷采用潤油技術,如同敷面,可以讓紙張保持永久的潤感。新的影印本,不僅全部原大影印拓本正面,反面褙紙也原色影印,就連上下的裁口,以及左側的裁口,都原色印制,這樣可以說是最為忠實地呈現出原冊的現狀,做到“幾同真跡”。
附冊簡潔,標題醒目。除去正冊之外,附冊包含兩個部分,一為南京大學博物館撰寫詳細介紹;一為文物出版社撰寫后記,其在南大博物館文章之外,補敘未盡之說。二者讀來,互為補充,用心巧妙。本書之標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宋拓大觀帖第六卷榷場本”“晉王羲之書”包括傳拓年代、帖名、卷數、宋代拓本交易地點、書寫人,諸多內容,可以讓讀者對拓本的基本信息一目了然。
《大觀帖》可以說是《淳化閣帖》的升級版本。今天,《淳化閣帖》第六卷傳世未見原刻本,所謂宋拓,也都是翻刻,不能和《大觀帖》卷六同日而語。啟功先生生前,曾多次希望文物出版社能聯合南京大學博物館出版此卷,然而都未能達成較為理想的結果。這次的影印,封外的題簽,采用啟功先生早歲在《大觀帖》卷六影印本上題寫之字,也算是對先生最好的懷念吧。20世紀80年代,先生曾盛贊日本二玄社的影印技術,今天若能見到文物出版社出版如此精美的《大觀帖》影本,一定會引以為豪,寫下觀后感言。
如果說本次出版有如此多可圈可點之處,在這里,也應提出更高的期望:若能聯合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將其余八冊《大觀帖》真本高清掃描,搜尋已佚的《大觀帖》第十卷黃賓虹藏本,加之出版《太清樓書譜》吳乃琛本,成《宋太清樓帖傳世真本全編》,以物美價廉的精品奉獻給讀者,當為真正的文化傳承!
(作者:高巖,系清華大學中國書法與文化研修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