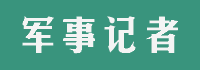借力揚聲:發出中國共產黨堅定抗戰的時代強音——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輿論斗爭的實踐與思考
摘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這既是歷史的鏡鑒,也是新時代在國際輿論場贏得主動的關鍵。本文分析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向國際社會傳遞真實情況和聲音的實踐,探索新時代借力揚聲新路徑,旨在把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要求落到實處。
關鍵詞: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輿論斗爭
輿論斗爭是不同意識形態的思想交鋒和話語較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復雜嚴峻的輿論環境: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為掩蓋侵略本質,精心炮制“理論-媒介-文化”的三維輿論滲透機制,通過杜撰“大東亞共榮圈”“中日親善”等所謂理論,設立滿洲國通訊社、中華聯合通訊社等媒介,打造殖民敘事,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消解民族認同,將血腥的侵略戰爭美化為“文明傳播”,壟斷占領區輿論;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憑借其執政地位,對中國共產黨抗戰活動構筑“制度-技術-渠道”的三重輿論封鎖壁壘,成立戰時新聞檢查局、出臺各種限制性辦法規定,刻意制造信息圍堵與輿論打壓。日本侵略者的輿論謊言和國民黨的輿論封鎖,使國際社會對中共抗戰實踐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諸多誤解與偏見。針對這一困局,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采取借力揚聲策略,不僅成功打破信息壟斷、向國際社會傳遞抗戰真實情況,更呈現了中國共產黨進步政黨形象,對戰后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本文以該歷史范本為研究對象,深入剖析其借力揚聲的成功經驗,提出著眼傳播主體拓展、話語升維、情感賦能,探索新時代借力揚聲新路徑,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旨在把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要求落到實處。
一、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抗戰時期,由于客觀條件限制,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信息傳播與輿論引導中處于弱勢,借力揚聲是其突破傳播困境、拓展政治影響的重要戰略選擇。
(一)利用國際友人“他者敘事”,搭建信任傳播橋梁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通過積極團結國際友人,創造了生動的“借他者之口,傳中國之聲”的輿論實踐。一是邀請國際傳播使者,突破輿論封鎖。中國共產黨通過宋慶齡等牽線,主動邀請進步記者訪問延安。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沖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他根據這段經歷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等著作,在國際輿論場產生較大影響,擴大了第三方敘事的國際影響力;二是引導國際觀察團,塑造客觀認知。1944年,中國共產黨積極組織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等媒體的記者,在陜甘寧邊區進行了全面考察;三是聯動國際友人發聲,反擊輿論抹黑。針對國民黨“游而不擊”等污蔑,通過記者招待會、專題座談會等活動回應國際關切,系統解答國際社會對中共抗戰戰略的疑問,如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葉劍英所作的《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等,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的污蔑言論。
將國際友人轉化為“他者敘事”載體,印證了傳播學中的“第三方背書效應”—非利益相關方的客觀視角更易獲得受眾信任。在國際輿論場波譎云詭的今天,我們更要借鑒抗戰時期“他者敘事”的智慧。要遴選具有較高可信度和國際影響力的“他者”群體作為敘事主體;要以其良好的聲譽和專業背景,為傳播內容提供有力背書;要讓可信賴的“他者”成為中國故事的“擴音器”。
(二)聯動國際組織“政治聲援”,強化多邊話語支撐
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有著重要影響力。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努力向國際組織展示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和重要性,匯聚道義力量、凝聚國際共識。一是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傳遞抗戰訴求。1938年2月,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在倫敦召開,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參會資格,推動吳玉章出席大會并作《中國抗日戰爭的新階段》報告;二是凝聚國際力量,揭露侵略罪行。1942年8月15日,“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暨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大會”在延安召開。經過思想改造的被俘日本士兵以親身經歷為基礎的發言,揭露戰爭罪惡、表達對和平的渴望,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三是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升話語權。1945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參與了《聯合國憲章》起草,將民族自決、平等互利等理念融入國際準則。
聯動國際組織發聲體現了信源可信度原理。當今國際輿論博弈,我們更應加強與權威國際組織合作。要借助國際平臺闡釋中國理念、中國方案;要通過具有較強公信力的國際渠道和資源,如官方文件、報告、會議等,傳遞中國立場、表達中國態度;要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規則制定,推動中國主張成為國際共識。
(三)發揮華僑同胞“愛國勢能”,拓展海外傳播網絡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敏銳洞察海外僑胞對祖國的拳拳赤子之心,通過這根血脈相連的情感紐帶,構建起強大的跨國傳播網絡。一是借力僑資媒體,傳播抗戰主張與事跡。中國共產黨積極與僑資平臺合作,聯合《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華僑日報》等媒體,開設抗戰專欄,系統闡述中共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理論等核心主張;二是構建僑團聯絡組織。中國共產黨主導成立僑胞抗日團體,推動“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等組織建立,以《松花江上》《黃河大合唱》等文藝作品喚醒民族記憶,增強情感聯結;三是邀請僑胞實地考察。1940年,海外華人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應邀到延安訪問,其后發表《西北之觀感》演講,引發了轟動。
同根同源更能共情共鳴。海外僑胞對中華文化與國家發展有著更多的認同感,要明確其“民間外交使者”的社會角色定位;要完善激勵機制;要喚醒情感共鳴,助力將愛國情懷轉化為傳播力量。
二、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的科學性和群眾性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實踐并非偶然之舉,而是深度契合傳播學原理的戰略選擇。
(一)借媒介之力,“意見領袖與信息中介”的雙重驅動,讓抗戰主張跨越國界精準觸達國際受眾
媒介在輿論中具有過濾、引導、塑造等作用。抗戰時期,埃德加·斯諾對毛澤東關于“持久戰”戰略的詳細記錄和傳播,有效糾正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悲觀認知;記者福爾曼撰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從軍事專業視角論證了敵后戰場價值;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為樞紐,與路透社、合眾社等國際通訊社建立的良好合作關系,更直接助力中國共產黨抗戰理念的廣泛傳播。這啟示我們,在國際傳播領域,媒介是跨越文化與地理隔閡、傳遞信息、塑造形象、影響輿論、促進文化交流與理解的關鍵橋梁和工具。善借媒介之力,能夠增強國際話語權。要打造親歷者權威敘事,通過“第一手資料”構建權威信源,以意見領袖的“在場式”敘事觸達國際受眾;要建立多元意見領袖矩陣,從不同角度解讀,讓信息觸達更多受眾;要構建跨國網絡節點布局,打造多元化信息中介平臺,通過官方媒體準確發布權威信息、社交媒體及時互動擴散、智庫提供專業研究支撐、意見領袖引導輿論方向等,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信息傳播體系。
(二)借話語之力,“議題設置與框架理論”的協同運用,重塑中國抗戰的國際敘事邏輯
話語既是通道,也是武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巧妙將議程設置與框架理論融入輿論斗爭實踐,通過系統化、策略化的話語構建,有效引導國際輿論走向。例如,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把捍衛國家主權的斗爭與國際社會對基本價值的追求相統一,使抗戰話語突破文化與意識形態隔閡。其成功實踐對于當下有著啟示意義。國際傳播中,掌握輿論主導權,要錨定核心議題,主導國際輿論議程;要構建傳播框架,重塑國際敘事;要創新話語表達,增強輿論引導效能。
(三)借情感之力,“情感傳播與社群動員”的聯動效應,形成跨越山海的輿論共振
情感既是凝聚人心的紐帶,也是激發行動的動力。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民族認同為根基,推動民眾情感能量向抗戰支持行動轉化。例如,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等事件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系統收集日軍暴行的影像、證詞資料,通過揭露日寇暴行,激發民眾悲憤反抗情緒。又如,中共中央先后設立海外工作小組、華僑救國聯合會、中央華僑工作委員會等,通過書信、廣播、海外聯絡站等渠道,定期向僑胞通報家鄉抗戰進展、根據地建設成果,不僅打造了精神共同體,還獲得了源源不斷來自海外的物資支持。這啟示我們,情感傳播能夠增強信息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共鳴與連接,進而推動信息更廣泛地傳播并引發受眾的情感反應和行為改變。國際傳播中,我們一方面要善于將情感認同轉化為合作動能,深入挖掘和平、互助等人類共通的情感價值,依托社交媒體搭建情感聯結平臺;另一方面要激活海外僑胞、國際友人等社群力量,擴大中國聲音傳播半徑。
三、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力揚聲的輿論斗爭實踐,既展現了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戰略靈活性,也蘊含著深刻的輿論斗爭規律。
(一)構建聯動矩陣,多元協同凝聚傳播合力
構建聯動矩陣,多元協同是突破信息封鎖、增強話語影響力的核心路徑。如前所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整合國際友人、國際組織機構與海外民間力量,構建起層次分明、功能互補的第三方傳播體系。特別是聯系民間群體,有效規避審查封鎖,實現信息的滲透式傳播,為當代國際傳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全媒體時代,信息傳播主體多元化、渠道多樣化、受眾分眾化,“去中心化”特征更為明顯。要積極培育國際意見領袖、學術共同體等第三方力量,以“他者視角”講述中國故事,提升話語可信度與穿透力;要聯動多方,打造多層次協同的傳播網絡范式,以傳播密度提升傳播效能;要激活民間資源,挖掘“草根傳播者”潛力,將民間智慧轉化為官方話語傳播的補充力量,以個體敘事承載集體價值,構建剛柔并濟的傳播格局。
(二)升級話語體系,多路并進探索敘事創新
議題設置的前瞻性、框架構建的創新性與話語選擇的適配性,是突破輿論困境的關鍵要素。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敏銳捕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時代主題,將“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確立為核心議題。這種設置,把中國戰場的戰略價值與全球反法西斯大局緊密綁定,將本土議題轉化為具有普世意義的公共議程,將本土抗戰實踐轉化為具有國際共鳴的傳播話語,為突破信息封鎖提供了經典范式。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主動把中國話語嵌入國際敘事鏈條,以國際受眾的認知邏輯為切入點進行議題關聯,使中國理念從“被認識”到“被認同”;要加強框架創新,摒棄被動回應的話語策略,主動以事實為支撐,重構議題敘事邏輯;要注重話語的適配性,考量目標受眾的文化背景和思維邏輯,針對不同受眾群體采用差異化話語策略,讓信息精準觸達受眾。
(三)強化情感賦能,多點觸達深挖傳播潛能
穿透輿論迷障,情感始終為關鍵紐帶。中國共產黨通過精準共情直擊受眾心理、分層遞進培育戰略信任、符號沉淀凝塑深遠影響,成功打破認知桎梏,化第三方力量為輿論同盟。例如,邀請外國記者實地采訪,以“延安窯洞的燈光”象征革命理想,借外國記者鏡頭和海外僑胞口述將這些符號傳播至國際輿論場,利用認知符號理論中“符號承載意義、強化記憶”的特性,使中共積極抗戰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這啟示我們,要精準定位情感靶點,針對不同第三方群體的心理特質,構建差異化情感共鳴點,打破認知壁壘,使情感符號與文化語境精準適配;要逐級夯實信任支點,根據受眾認知特點與情感距離,設計階梯式傳播路徑,采用“漸進式情感滲透”的策略,將抽象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共情的具象體驗,推動受眾從“旁觀者”向“參與者”轉變;要以符號鐫刻記憶錨點,深度挖掘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價值符號,降低受眾理解成本,增強信息的辨識度與留存率。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責任編輯:張和蕓